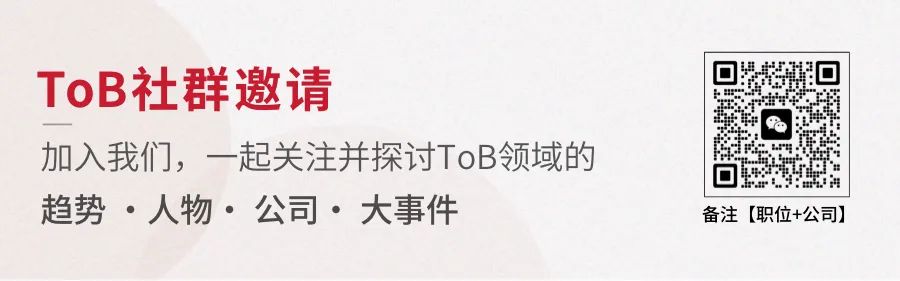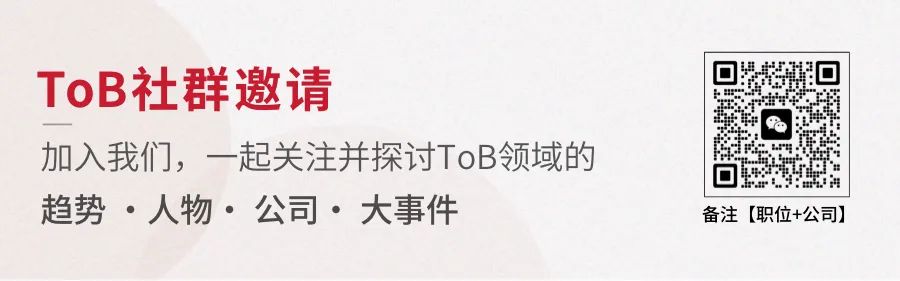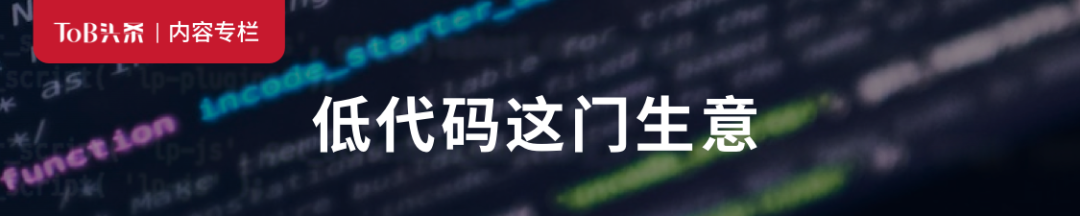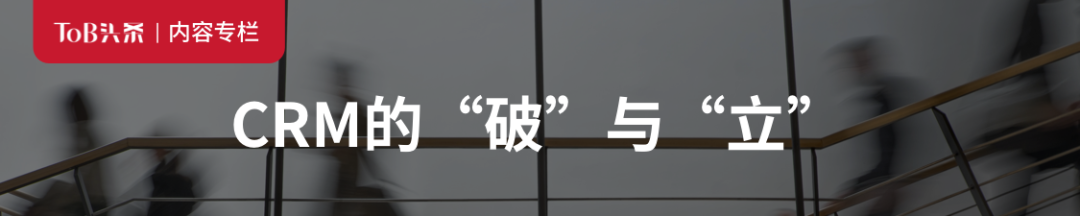按照陈玮的观点,科技创新的路子要能够走通,需要两条逻辑理顺:其一是科技成果产业化,让优秀的人才愿意创业;其二是金融股权化。
最大的堵点在于退出
陈玮认为,退出是一个指挥棒,因为退出环节受政策、监管和引导强相关的。如果退出堵点不解决,募资、投资、管理等都将成为问题。退出解决好,其他就相对容易。而二级市场内就是退出的核心所在,正如他所言:“股市好一切都不是问题,股市不好一切都会成为问题。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
在李丰看来,退出本质是连通效率的问题。最直接的方式,是提高一二级市场的连通性。从国际惯例上看,60%的被投项目获得回报,是依靠兼收并购退出。30%是依靠基金份额转让。只有小于5%的数量是依靠IPO上市退出。在过去,中国资本市场的估值逻辑,是以盈利性考核为主,净资产为辅,再配以适当的成长性。但是这套估值逻辑难以给当下高科技公司定价,所以并购、S基金都难以成型。中国资本市场还需要一段时间调整,才能以成长性来估值,才有上市公司愿意去收购高成长性的高科技企业。由此,60%的兼收并购退出方式才能成为可能,另外30%的退出方式也水涨船高,最后那5%的上市退出自然也就通畅了。以上观点与杨晓磊的看法一脉相承,“我们的退出结构比较单一,基本靠IPO退出。而美国从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开始,就不太依靠IPO退出解决行业的流动性。如果国内有足够的并购人才、金融和政策等支持,未来才会逐渐形成一个良好的退出生态。”更进一步,为什么二级市场不好,或者不能按照成长性企业进行估值呢?米磊的观点是,因为过去20年,一级市场没有投资真正的硬科技公司,导致今天二级市场企业的质量普遍堪忧。所以在他看来,当下一级市场的堵点根源在于历史:风险投资在过去20年是否真正在做正确的事。
创投在国民经济中究竟是何地位
当然,退出并不是唯一的堵点。中国投资协会股权和创业投资专委会会长沈志群的观点是,创投的地位问题迟迟没有解决。
20多年来,中国创业投资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地位和定位迟迟没有确立。国家统计局的行业统计分类当中,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创业投资。在立法上,2005年我国颁布了《国家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到今年为止已经施行了19年,但却没有进一步发展。行业一再呼吁加快创投立法。因为只有明确了创业投资的地位与定位,募投管退的堵点才能得到有效解决。沈志群的观点鞭辟入里,核心是回到原点,确立创业投资的本质属性。因为只有回答创业投资“是什么”,才能解决“如何发展”的问题。发起回购意味着双输
站在创业者的角度,当下最为关心的“堵点”,无疑是对赌与回购。“泛化的对赌条例,为创业造就了一个非常不友好的环境。应该从政策或立法层面,对创业者的基本生存权利提供保护。”北京他山科技的创始人孙滕谌在节目的发言环节,提出了他的担忧。这一问题,启明创投的邝子平此前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进行讨论。投中信息CEO杨晓磊借用此篇文章总结说,回购条款因为都是舶来的,它在使用的时候一定有个前提的,这个前提是不要伤害公司的运营。但今天不少机构使用这个条款的时候,把它延伸化了。科技部资源配置与管理司副司长沈文京,专门组织团队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调研。根据调研情况显示,“监管的要求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目前类似的情况还比较多。”从政策端,管理部门正在推动有关部门优化国有的特别是中央层面的基金,能够适当延长存续期。同时优化国有创投机构的考核激励办法,使国有资本真正成为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但适度的监管也是必要的”,毕竟投资机构“管理着大家的血汗钱。”陈玮的观点是“只要发起回购,就意味着双输”,投资人和创业者都不愿意走到那一步。核心是回到退出的关键点上:只有当退的堵点解决了之后,其他问题都迎刃而解。“当我有100个项目,20个项目IPO了,已经非常赚钱了。所以出现了10个问题项目的时候,大家的宽容度也会越来越强。”如何破题:专业化、生态营造和耐心资本
如何破除以上堵点?专业化、高质量、生态是6位投资人提及最多的关键词。
投资机构、监管部门都需更加专业化
方建华认为创投行业正在发生从财务投资人到产业投资人的深刻转变。风险投资行业前期主要依靠移动互联网红利,以财务投资人为主。而今天正在要向产业投资人、CVC去转变。
投资机构不是简单的投钱,最后从企业要报表,等着企业IPO来获取红利的过程。而是一个“价值发现、价值实现的过程。”更需要机构陪伴企业、赋能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成长。从过往的历史看,各监管部门的规章制度打架并不鲜见。风险投资行业总体上管理得多,支持得少。陈玮感慨地说,为什么这次出台政策,让大家觉得信心一振,仿佛看到了彩虹和春天?正是因为现在是以发展为主的态势。而且,“如果有专业的LP、专业的募资投资,还有增资服务的专业化,退出环节、监管二级市场也用专业化方式做,高质量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专业化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回到投资的本质。杨晓磊补充说,投资天然是要赚钱的,没有造富效应,不可能有更多的资金涌入到创投市场来。他以《风险投资史》举例:传统金融机构是基于历史推测未来,规避小概率事件,风险投资是抛掉历史去追逐小概率事件。因此风险和收益天生就是跷跷板的两头,风险越高,原则上收益越高。所以创投领域一定要赚钱。米磊则将“生态”看做是破题的关键。其一,创业投资属于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一个环节,除了科研端和产业端,最核心的短板现在成了创业投资。所以国家鼓励创业投资,是需要将整个创新生态营造得更好。第二,对投资机构的小生态而言,也面临的募投管退的卡点。比如更耐心、关注长期主义的LP增加将大大有利于小生态的建设。小生态好了,行业也会变得更好,甚至影响整体大生态。而更耐心和长期主义的LP,则在耐心资本的话题上成为了共识。
耐心资本,需要时间、能力、机制和信心
为什么在过去的20年,中国市场缺乏长期资本、耐心资本?
在深创投总裁刘苏华看来,以前中国的发展阶段依靠要素驱动,对于长期资本的需求并不迫切,但现在中国突然卷入到创新驱动,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就变得非常重要。而且要做好耐心资本,关键是敢冒风险,善冒风险。因为耐心意味着周期要长,时间长了肯定不确定性多,所以一定要敢冒风险。同时,需要通过专业性提升来减少不确定性,所以是善冒风险。刘苏华的观点对于国有资本更具指向性。目前掌握资本的机构大部分是国有资本,但很多国有创投机构不敢投资。他举例而言,过去内地投资机构到深圳调研,经常问到深创投一个问题,“你们怎么做尽职免责的?我说我们没有细则,我们靠信仰。”“深圳几十年历史,我们统计过,从来没有谁因为创新、因为纯粹的经营事物而追究谁的责任。”这一方面说明了深圳在创业投资上走在前列,但也说明对于大部分国资机构而言,如果能够出台相关的尽职免责实施细则,则更能帮助国资在创业投资上大展身手。这也是行业内亟需解决的机制问题。机制问题,正是李丰所关注的。他认为耐心资本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能否理解并完善相关机制。他举到了险资的例子,保险LP是难得的长钱。但是在其财务考核中,“有个每年需要回笼的现金数量,这就对大家在管理资金上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此在长钱的基础上,需要一些具体的机制,使得LP能够匹配到他自己行业内的监管要求和上级监管要求。当然,对于耐心更直观的要求则是时间。正如陈玮的看法,时间是衡量耐心的重要尺度。而且行业中可喜的迹象是,很多国有基金,把基金年限延续到10年以上。只有“基金原则上不低于10年,天使基金不低于15年,这样耐心资本才能够真正形成。”在沈志群看来,耐心则与信心同行。“没有信心就没有耐心”,投资人应该对现在的困难和局势有充分的耐心,这来源于对中国科技创新的信心。而且只有拥有信心才能够留在牌桌上。正如投中信息CEO杨晓磊所言,我们希望行业更耐心一点,甚至忍耐一点。今天有可能正在曲线的左侧,离场是特别不理智的行为。只有大家都存在于这个市场,持续为市场做贡献,才有可能形成强烈的共识。